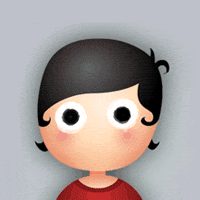【学术争鸣】再评张继龙《阿勒坦汗与土默特》:低级抄袭
再评张继龙《阿勒坦汗与土默特》:低级抄袭
晓克
(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)
张继龙《阿勒坦汗与土默特》一书(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,2016年3月,以下简称《阿勒坦汗》),存在着许多明显的“低级抄袭”现象。
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《关于如何认定抄袭行为给某某市版权局的答复》(权司[1999]第6号)对抄袭作出了明确界定:“《著作权法》所称抄袭、剽窃,是同一概念(为简略起见,以下统称抄袭),指将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窃为己有。……因此,更准确的说法应是,抄袭指将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窃为己有发表。”抄袭有低级、高级之分:“从抄袭的形式看,有原封不动或者基本原封不动地复制他人作品的行为,也有经改头换面后将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成份窃为己有的行为,前者在著作权执法领域被称为低级抄袭,后者被称为高级抄袭。”
对于“低级抄袭”,学界早有共识。有论者认为:“抄袭者一般都存在大量引用他人的作品,大都原封不动地改头换面或略微改动地整章、整节或整段地采用他人的作品,这种情况在著作权执法领域被称为低级抄袭,本文在此不作赘述。”
下面来看张继龙《阿勒坦汗与土默特》一书中的“低级抄袭”情况。
《阿勒坦汗》第1页左栏第一自然段:
“土默特”一名出现于北元时期,用以指代土默特部落集团、万户,清朝时指称归化城土默特旗以及喜峰口外的土默特旗。
《土默特史》第64页第一自然段:
“土默特”(Tümed)一名出现于北元时期(明代),用以指代土默特部落集团、万户,入清指称归化城土默特旗以及喜峰口外土默特旗。
上揭《阿勒坦汗》的这段文字,构成该书开篇第一自然段,它竟然是这种“低级抄袭”的产物,真使人感到匪夷所思,难以置信!
尽管是“低级抄袭”,但还是出了问题。所谓“土默特部落集团”,这一学术概念是1984年本人在硕士学位论文中,根据苏联学者Б.Я.符拉基米尔佐夫关于蒙古部落集团的论述提出的。该概念是指,从15世纪70年代开始到16世纪初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之前右翼蒙古三大部落集团之一,这个部落集团的名称为“土默特”,是“土默特万户”的前身,所以称“土默特部落集团”。它只是一个现在的学术概念,而不是可见于蒙古文、汉文史籍中的固有名称。《阿勒坦汗》认为:“所以,‘土默特’应是阿勒坦汗的‘十二土默特’形成后出现的,而不是单一的部落名称。这一名称……没有实质意义”。(第4页)“而明代汉籍史料之所以没有‘土默特’的记载,一是因为‘土默特’一称出现较晚,二是因为‘土默特’并没有实质所指。”(第3页)可见,该书作者张继龙认为,在阿勒坦汗(1508~1582年)成为部落首领之前,是不存在“土默特”的。那么,上揭《阿勒坦汗》第1页第一自然段中的“土默特部落集团”这一概念是从何而来,又是指何而言?
《阿勒坦汗》第3页右栏第2自然段:
在1662年成书的《蒙古源流》中,反映出来的情况是15世纪70年代,土默特和蒙郭勒津两个名称就可以互相通用了。
《土默特史》第81页:
在蒙古文史籍中反映出来的情况是,15世纪70年代,“土默特”和“蒙古勒津”两个名称就可以互相通用了。
这两段文字主体部分表述相同,语义也完全一样。二者的区别在于:前者把后者所说的“在蒙古文史籍中”,随便改为“在1662年成书的《蒙古源流》中”。从事这段蒙古史研究的人或认真读过《蒙古源流》的人都知道,在《蒙古源流》相关记述中,是反映不出来上述情况的。原因很简单:在《蒙古源流》中,不要说缺乏与之有关的直接记载,即使是可以据之研究分析后得出上述结论的间接记载也难得一见。上述文字的核心部分虽然简短,但却是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,而不是直接见诸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。实际情况是,这个结论是在1984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《明代后期蒙古土默特万户的各部落及其驻地》一文中,经过对蒙古史籍无名氏《蒙古黄金史纲》和罗布藏丹津《蒙古黄金史》二书(学界有时合称“两《黄金史》”)的相关记载研究后得出的。有原文为证:“根据两《黄金史》的有关记载可以看到,在达延汗击杀癿加思兰之前,‘土默特’一名和‘满官嗔’一名就可以互相通用了。”“两《黄金史》把满都鲁汗派人剿杀癿加思兰之事错误地记在了达延汗名下了。……那么,‘土默特’和‘满官嗔’两个名称可以互相通用的现象应该是在满都鲁汗时代就已经存在的。”满都鲁汗时代”,是指满都鲁汗在位的1475-1479年。1986年,我发表《明代蒙古土默特万户出现的历史过程》一文,其中说道:“如上所述,,亦即十五世纪七十年代,‘土默特’和‘蒙古勒津’两个名称就可以互相通用了。”这就是这一结论的由来。至于《土默特史》中所说的“蒙古文史籍”,只是在撰写《土默特史》时,为了行文方便而采用的简洁说法,实指“两《黄金史》”而言。不知张继龙根据什么,将其妄改为“1662年成书的《蒙古源流》”?又是如何从中看到上述情况的?
如果读者认为以上比对文字较短,难以说明问题,那就来看看较长的:
《阿勒坦汗》第169页左栏:
副总兵李联芳战死。此后,火落赤和真相台吉等又率兵围攻河州、临洮、渭源,总兵刘承嗣率七千余兵与之周旋。明军先有几次小胜,但朱家山一战,明军大败,损兵折将,游击李芳战死,总兵刘承嗣的盔甲中流矢四枝,幸免一死。在此之前的几次战斗中,战死的明军将领还有刘子都等七名千户。蒙古军大掠环洮河数百里以及临洮、渭源等地,明朝西陲大震。
《土默特史》第195页:
副总兵李联芳战死。此后,火落赤集合真相台吉、克臭台吉等“海部”首领,率众攻击河州、临洮、渭源,总兵刘承嗣率七千余兵与之周旋。明军先有几次小胜,但朱家山一战,明军大败,损兵折将,游击李芳战死,总指挥刘承嗣的盔甲中流矢四支,幸免一死。在此之前的几次战斗中战死的明军将领还有千户刘子都等七人。蒙古军大掠环洮河数百里以及临洮、渭源等地,明朝西陲大震。
还有必要再对上述两段文字之间的关系作什么说明吗?需要指出的是,张继龙在上面那段抄袭文字后面,又加了一句:“这就是隆庆和议后蒙明发生的,明朝称之为‘洮河事件’。”这画蛇添足的一笔,却造成如下错误:1、隆庆和议后,蒙古和明朝之间曾多次发生过大大小小的,而不仅仅是这一次。因此,准确的说法只能是:这就是隆庆和议后蒙明之间发生的一次;2、所谓“明朝称之为‘洮河事件’”,也有问题。遍查《明实录》、《明经世文编》、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及《明史》等许多有关明代的史籍,均未见“洮河事件”一语,只有在《明史》卷228《列传》第116中有一句“洮河之变”的说法,也仅此一见。看来,明朝人并未称道过什么“洮河事件”,所谓“明朝称之为‘洮河事件’”,又是该书作者凭空想象而杜撰出来的。为了掩人耳目,抄袭时是要尽可能对原文作一些改动的。而在改动过程中,懒得下功夫去核对资料,只是信手拈来,随意改写,不出错才是怪事呢。
目前,笔者尚未完成对《阿勒坦汗》与《土默特史》的比对,大约只比对了三分之二的篇幅,初步统计,类似这样的“低级抄袭”已有数十处之多。
《阿勒坦汗》的作者不仅如此对待《土默特史》,对待其他相关论著也毫不客气,照样去“低级抄袭”。试举几例如下。
《阿勒坦汗》第222页右栏:
卓尼·曲吉·金巴达吉生于1574年,于1641年去世。关于他的生平事迹,在《安多政教史》中有较详细的记载。他是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中部洮河上游卓尼大寺的高僧。。起初,卓尼大寺是萨迦派的一座小寺院,明代天顺年间,卓尼第二代土司时改为格鲁派寺院。卓尼·曲吉·金巴达吉十三岁出家,后到色拉寺学经,获得色拉寺麦巴扎仓的噶久名号。然后在上密院学习的时候,他和迈达里呼图克图被选任派往蒙古地区。
乔吉《蒙古史·北元时期(1368~1634)》(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8年4月,以下简称《蒙古史》)第88~89页:
卓尼·曲吉·金巴达吉(1574~1641)事迹:
关于这位高僧的生平事迹,在藏文《安多政教史》中有较详细的记载。他是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中部洮河上游的卓尼大寺的高僧。,起初是萨迦派一座小寺院,到明代天顺年间(1457~1464)卓尼第二代土司时代改为格鲁派寺院。他十三岁出家,后来到卫地色拉寺(se-ra-dgon-pa)学经,获得色拉寺麦巴(smad-pa)扎仓(grwa-tshang 僧院)的噶久(dkav-bcu)名号。然后在上密院(rgyud-stod)学习的时候,他和上文所叙东科尔呼图克图、,派往蒙古地区。
两相对照,尽管《阿勒坦汗》的行文在副词、介词等无关紧要之处略有变动,但“低级抄袭”的手法还是昭然若揭。如上所述,抄袭往往会出错。张继龙将乔吉先生所说:“他和上文所叙东科尔呼图克图、,派往蒙古地区。”妄改为:“他和迈达里呼图克图被选任派往蒙古地区。”不仅丢掉了“东科尔呼图克图”,而且还使原来很通顺的话语变成了病句:“选任”和“派往”都是动词,“派往”可以和“蒙古地区”搭配,“选任”却不能与之搭配。那么,上述三人被“选任”为了什么?没有了下文。
《阿勒坦汗》对《蒙古史》的类似抄袭还有很多,读者若有兴趣,可以自己先行对照阅读二书,或者容待笔者日后另行评论。
再看《阿勒坦汗》对李文君《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》(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2008年11月)的“低级抄袭”。
《阿勒坦汗》第175页左栏:
……方逢时认为,通贡互市是处理明蒙关系的最佳方法,绝不能因兵都台吉犯边影响了明蒙互市的大局。内阁辅臣张居正对青海蒙古开市一事也比较开通,他在给甘肃巡抚侯东莱(字掖川)的复信中说:“西海开市一节,望公熟计而审处之,窃以为此地见与番人为市,何独不可与虏为市,前任寥君(指寥逢节)拘泥而不达于事变,其言不可为市,不过推事避患耳,非能为国家忠虑者也,但彼既有不逊之言,在此时未可便许,且俟俺酋戒谕之后,果帖服无言,待其再乞,然后裁许,则绥怀之恩出于朝廷,而非由于要索矣!”这就是说,宣、大、延绥已经开始互市,那么不能因小失大,甘肃也可以开市,但是要把握好时机,让兵都等人明白,给你开市是天朝的“恩赐”,并不是你武力威胁的结果。
李文君《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》第204页:
方逢时认为,通贡互市是处理当时明蒙关系的最佳方法,绝不能因丙兔台吉一个人影响了明蒙互市的大局。内阁辅臣张居正对给西海蒙古开市一事也比较开通,他在给甘肃巡抚侯东莱(掖川)的批复中说:“西海开市一节,望公熟计而审处之。窃以为此地见与番人为市,何独不可与虏为市。前任寥君(指寥逢节)拘泥而不达于事变,其言不可为市,不过推事避患耳,非能为国家忠虑者也。但彼既有不逊之言,在此时未可便许。且俟俺酋戒谕之后,果帖服无言,待其再乞,然后裁许,则绥怀之恩出于朝廷,而非由于要索矣!”②宣、大、延、宁已经开始互市,那么不能因小失大,甘肃也可以开市。……就是找一个把握主动的最佳时机,……让丙兔台吉等人明白:给你开市是天朝“恩赐”的结果,并不是你武力威胁的产物。
二者稍加对比就不难看出,前者对后者的抄袭到了多么“低级”的程度。但还是有些需要略加说明之处:首先是对原文内容的妄改。张继龙将李文君原文中的“宣、大、延、宁已经开始互市”,改为“宣、大、延绥已经开始互市”,“宁”、“绥”妄改一字,便将原文中包含的宁夏边外的互市彻底抹杀了,从而歪曲了原作原意。其次是标点符号的运用。李文君在所引张居正的批复中,正确地使用了标点符号,而在张继龙所引张居正的“复信”中,真正是“一逗到底”,完全忽略了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。
对于永发《志之余》(远方出版社,2001年9月)的抄袭。
《阿勒坦汗》第356页右栏第一自然段:
清编呼和浩特《土默特旗志》的职官表共列144人,无一姓云者。民国以后,云姓渐多。1923年,在北京蒙藏学校就读的土默特青年共43人,其中以“云”、“荣”为姓的15人。到1935年,土默特呈报蒙藏委员会的《职官表》共列134人(兼职重名者不计),有汉姓者67人,其中云姓22人,可见时代愈晚,云姓增加愈多。
于永发《志之余》第247页:
清编呼和浩特《土默特旗志》的《职官表》共列一百四十四人,无一姓云者。……民国以后,云姓渐多。例如1923年在北京蒙藏学校就读的土默特青年共四十三人,其中云姓十五人(按:本地云、荣发音相同,且同一家族兼有云、荣二姓,为统计方便,姑且视为一姓),占35%。到1935年,土默特呈报蒙藏委员会的《职官表》共列一百三十四人(兼职重名者不计),有汉姓者六十七人,其中云姓二十二人,占32.8%。可见时代愈晚,云姓增加愈多。
张继龙在上文中,除了将于永发先生的按语删掉,把汉字数字改为阿拉伯数字外,基本原封不动地抄袭了《志之余》,实可谓“低级抄袭”。尽管如此,他还是把于永发先生原文中的“《职官表》”改为了“职官表”。虽然只是相差一个书名号,但表达的意思却并不相同,《职官表》是被引用文献的名称,“职官表”却没有了这层意思。
我的第一篇评论文章《初评张继龙﹤阿勒坦汗与土默特﹥:抄袭问题》,登载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微信公众号“朔方论坛”上之后,有网友留言说:“如果是引用并注明出处就不算抄袭”。此话有一定道理。关键问题是在《阿勒坦汗》全书中,竟然没有一条注释,对于“引用”别人的研究成果也没有任何说明。在该书中,存在着太多学术不规范现象,原打算对其中学术规范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专题评论,所以,在第一篇评论文章中没有对该书全书不作注释的问题突出强调。结果,可能导致一些不太了解具体情况的读者,对评论中所指出的抄袭现象是否成立,还心存疑虑。这也很正常。为此,在这里先行指出其全书不出注释的学术规范方面的问题,以便消除读者在阅读评论文章时可能产生的疑虑。而对于包括注释问题在内的其它学术规范问题,笔者还会在以后进行专题评论。
近来,笔者利用手头现有的部分论著与《阿勒坦汗》作了初步比对,比对工作尚未完成。笔者就是根据已有的部分比对结果,撰写了第一篇评论和本文。今后,还会继续写文章对该书进行学术评论,欢迎诸位读者继续关注和参加讨论。
2016年8月4日
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:《关于如何认定抄袭行为给××市版权局的答复》,权司[1999]第6号。
吴启运 等:《关于如何界定学术论文中“合理使用”与“抄袭”的探讨》,《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》2002年第1期。
晓克:《明代后期蒙古土默特万户的各部落及其驻地》,油印本,第9页,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科,1984年。
晓克:《明代蒙古土默特万户出现的历史过程》,《内蒙古社会科学》1986年第5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