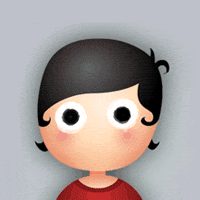我家的枣红骡子
我家的枣红骡子
王彦峰
枣红骡子是1988年来到我们家的,那时它还是个骡驹子,一家人对枣红骡子很是钟爱,父亲总是割最好的草给它吃,我和弟弟还时不时的抓一把豌豆、黑豆给它吃,看着它香甜地咀嚼,我轻抚它的脸,梳理着它光滑的皮毛。枣红骡子长大了,也能干活的了,播种、翻地、驮东西都成了它的事,每到开学,我的粮食、干粮、被褥都是枣红骡子驮着送往学校的。它干起活来很是卖力,从来不知道啥是累。我们全家也很喜欢它卖力干活的性格,村里人都说它是一头有“骡格”的骡子。
我感叹古人造字的神奇,在创造“骡”字的时候,似乎就决定了骡子的性格和命运,或者古人是根据骡子的性格和命运才创造了“骡”字,骡子就是“累马”,自然要比马和驴干更累更苦的活。它只要驮了东西、拉了铁犁就会奋力向前,不知道歇脚,不懂得偷懒。有句古语叫作“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”,言下之意是说马和骡子一比就会落下半截,我听了愤然不平,马和骡子各有所长,“遛遛”也要看怎么个遛法和溜什么?如果比跑的快,骡子自然不是马的对手,倘是负重、拉犁、长途跋涉,再好的马也没法和骡子比。骡子是那种忍辱负重,忠心耿耿,“堪托生死”的动物。
自从枣红骡子进了我家的门,日子就逐渐的富裕起来。茬地被它翻过,连个杂草根都没有。莜麦、山药、胡麻样样长得都好,年年丰收。放了暑假,我和弟弟争的放骡子,一是放骡子轻松,不用干活,二是骑骡子对我有着莫大的诱惑,我那时刚读了《说岳全传》和《杨家将》,还有一杆红缨枪,骑上骡子拿上红缨枪,自己俨然就是一名古代的将士,当一回少年英雄,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。放骡子也很有乐趣,把骡子牵到草地上钉锥之后,骡子拖着长长的缰绳转圈吃草,不会到处乱跑,吃完一处再牵到别的地方,这个时侯我们可以尽情地玩耍,不是抓松鼠,就是掏鸟蛋,或者烧山药,总之玩的很是快活。
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好了起来,我们兄弟也逐渐长大成人,安家立业,但是父亲老了,枣红骡子也老了,但它仍旧干劲十足,送粪、播种、犁地、碾场、驮庄稼样样不减当年,兢兢业业,一丝不苟。它不但干我家的活,街坊邻居、乡里乡亲,能帮忙的尽量帮忙。但它的需求甚少,只是一把青草……2013年以来,父亲给我打电话常说:“咱家的骡子老了,走路不欢了”,是啊,1987年出生的骡子活到2013年,已经走过了25个春秋,和人相比不能算老,但骡子到了这个年龄,已经相当于八十岁的老人了。春节我回到故乡,枣红骡子看到我回来,好像认出我来似的,冲我“咴咴”地叫着,突然间,我从它忧郁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悲伤,一颗晶莹闪亮的泪珠滚落下来,重重地砸在了地上,也沉沉地砸在了我的心里。
2014年夏的一天,我在睡梦中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:“咱家的骡子死了”,我一下子站了起来,悲伤的不知从何说起。妻子见我大惊失色,以为家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,听了我的解释后,她冷冷的说了一句:“至于吗。不就是头骡子,给家里寄钱再买一头”。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她哪里知道一头骡子在农家的分量,她又哪里懂得,我家那头枣红骡子在我们全家人心中的地位和感情。据后来弟弟讲,父亲是夜间给骡子添草时发现它死去的。它死时肚子涨得跟鼓一样,两只眼睛睁得很大很大,眼角里还淌着两行湿湿的泪水。父亲见到死去的枣红骡子很是悲伤,蹲在地上旱烟抽了一锅又一锅,很久都没有站起来,一连几天没有睡觉。我放暑假回到故乡,看到父亲背弯了许多,一下子老了许多。
枣红骡子离开我们一年多了,每当看到骡子,或是读到有关骡子的章节,我就会不由得想起它。虽然枣红骡子死后,我家又买了一头骡子,但它的圈一直空着,门也锁着,父亲不愿再打开圈门。亲爱的枣红骡子—你一路走好!你知道我为你写这篇文章吗?愿我们下辈子还是一家人。
作者简介
王彦峰:生于1975年12月,静乐县中庄乡人,中共党员,大专文化。1993年从军西北边塞,1999 年毕业于解放军西安陆军学院,2007年军转入警。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,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三届高研班学员,迄今已在《解放军报》、《国防》、《中国文艺》、《人民军队报》、、《甘肃日报》、《山西日报》等多家报刊杂志发表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新闻、评论、报告文学等作品3000余篇,出版文学专辑《边地星光》(上下卷)
识别二维码,一览“忻晋商”商城,你的宝贝就到家门口。